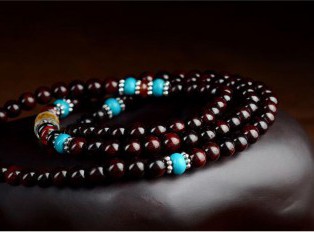听收藏专家马未都谈明清两代黄花梨家具,有说不尽的文化!
摘要:冰棍的名字质朴,现在叫雪糕,听着就小资,就矫情。冰棍的灵魂在冰,尤其在酷暑难耐的夏天,一根冰棍带有的凉爽不光是生理上的,更多是心理上的”。说着简单冰棍的是马未都,聊着古典黄花梨家具的也是马未都。看过太多关于明清黄花梨家具的文字,却从未认真聆听过马未都……虽是缺憾,却也不是不能弥补…
冰棍的名字质朴,现在叫雪糕,听着就小资,就矫情。冰棍的灵魂在冰,尤其在酷暑难耐的夏天,一根冰棍带有的凉爽不光是生理上的,更多是心理上的”。说着简单冰棍的是马未都,聊着古典黄花梨家具的也是马未都。看过太多关于明清黄花梨家具的文字,却从未认真聆听过马未都……

虽是缺憾,却也不是不能弥补。现在就有一篇文章能够让你领略“冰棍”的凉爽,同时触摸到“黄花梨”的文化厚度:
将一种自觉的追求完美地再现在家具设计上, 黄花梨家具是最具代表的。黄花梨家具在向人们展示华贵的同时, 又展示了一种其它木种所没有的耐性。这种耐性由不易开裂,不易变形,易于造型 , 易于雕刻等诸多优点构成。
黄花梨木显然也是文学名称,富于诗情。早在明时期,黄花梨就被称作花榈,花梨,在“讹音”中逐步流传下来。当民国初期替代品“花梨”出现后,黄花梨就成了正式名称并流传下来。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温润内敛的古典家具才又重新被人们所认识。尤其当德国人古斯塔夫·艾克的《中国花梨家具图考》问世后, 一股世界范围的收藏热逐渐蔓延,并持续了很久,直至1949年才告一段落。

1971 年 , 美国人安思远又有一本研究黄花梨家具的著作《中国家具》问世,国人尚且不知,国外早已捷足而行。1985年,王世襄《 明式家具珍赏》的问世,将黄花梨家具的研究与收藏再次推上了巅峰,海内外藏家均以收藏黄花梨家具而自豪。这样,明清两代黄花梨家具便堂而皇之地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博物馆内的新宠,成为新一代的古代艺术品。
在名贵木材中, 黄花梨家具比紫檀家具存世量大,品种也多。黄花梨家具常有一些“大家伙”存在,且面板宽硕无拼,足见黄花梨树之高大。明式架几案有宽达50cm,厚10cm,长350 cm的独板,全板不拼不接,纹理清晰流畅 , 俗称“一块玉”。这类朴素无华的家具明显可看出是为展示材料而制,这在中国古代家具的制作中并不多见。

纵观黄花梨家具,它的地域性特点似乎没其它木质家具明显,产生年代大约也限制在十七、十八两个世纪。然而它的品种多而全,家具中的椅凳类、桌案类、柜架类、床榻类、其它类等五类应有尽有,包括黄花梨小件在内, 可以说黄花梨家具足足风光了两百年。
能够认定为明代黄花梨家具的为数不多,许多专家认为的明代家具很有可能是清早期生产的。原因是在明晚期嘉靖万历两朝期间,宫廷家具均以漆器为主。我们在较为细致的晚期宫廷绘画中, 会发现漆制家具明显的华丽之风。

温文尔雅的黄花梨家具显然不具备华丽的特点,它所注重的是内在的表现力,这与晚明时期盛行的繁缛之风有些冲突。明朝自嘉靖起抛弃淡雅, 崇尚热烈,瓷器中的青花和五彩最具说服力,风格与漆制家具异曲同工。
明式黄花梨家具的魅力主要体现在简洁上,大部分黄花梨家具不做或少做雕花装饰,多文雅,少媚俗,这就是明式黄花梨家具文人化倾向的具体体现,也是近年来颇受收藏家和研究者喜爱的原因。

明朝晚期,由于政治上的腐败,文人对政治失去信心,寄情于生活享乐。加之资本主义的萌芽, 使得这时期的商品生产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市场的苛刻要求,文人的积极参与,使得黄花梨家具一经出现就羽翼丰满。即便是以令人挑剔的美学眼光看待,对明式黄花梨家具也是肯定多, 否定少。
貌似简单的明式家具却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它表达了一种文人注重内心世界,不意张扬的品质,这种优秀品质始终贯穿着明式家具的设计。

作为中国古典家具巅峰之作的明清黄花梨家具,我们有着太多述说不完的故事,即便是”收藏大王“马未都也未必能够说得尽。